文化随笔:黔东南乡镇与诗意电影语言
在当代文学艺术的创作理念中,乡镇作为乡村与城镇的融合,既保留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又展现了这二者的胶着,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载体。特别以视听为主要呈现形式的电影,运用大量的方言、民族服饰等小城镇文化意象,突出“乡镇”这一时空体难以侵入的神秘感与封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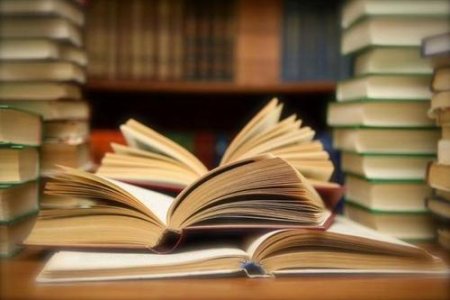
毕赣将这种族群地域特性作为构成其电影风格的重要元素,形成独特的电影话语。比如在视听话语层面上,镜面反射是毕赣电影中一个兼具技术性与文本性的表达手法。如在《夜晚》中,水面反射时针的拨动、湖面反射绿植的漂浮、后视镜反射人脸的悲怆,一切都敏感易碎,眼睛所见难辨真假,一切都只是宇宙的镜像。诸如此类的镜面反射也暗含了每个角色具有的双重意义:“万绮雯”和“凯珍”、罗纮武和“白猫”、白猫母亲和罗纮武母亲,他们之间都有着如同镜像一般真假难辨的共性与异性,一个角色承载着多重身份,暗含着多重时间线索,角色之间的身份关系就是影片文本的逻辑关系,这是毕赣电影中特殊的二重性乃至多重性的呈现。
另外,少数民族的地域性特色意象,如蜡染、芦笙、船只、苗乐等也多次出现在电影中,它们都将凯里营造出极致的孤独感和无法感同身受的忧思。而在诗性话语层面,诗意的表达是毕赣电影中最显著和独特的魅力。抛开导演和编剧身份的毕赣,也是一个年轻诗人,会将诗句适当地嵌入电影,使他的电影犹如诗集一般充满多样的解读,也平添了空灵气质。
电影《野餐》就是一部以诗歌连接场景的转换、用独白展现细微线索的作品。毕赣以贵州方言的诗歌旁白建立了电影话语表达的框架,用诗句为人物出场、时间线索、叙事细节一一定点。如“没有剃刀就封锁语言,没有心脏却活了九年”暗指陈升的九年牢狱生活,“手电的光透过掌背,仿佛看见跌进云端的海豚”解释前情中陈升对发廊老板娘的性暗示。毕赣还用陈升的第一视角来凝聚梦境,比如用手捂住手电筒的光,就是看到海豚的模样;陈升自述和妻子住在瀑布边,听不见彼此说话,只能跳舞;陈升坐在副驾驶与友人谈及曾经的牢狱经历。这些分解的叙事线索破除语言的逻辑性和排列秩序,模糊现实与梦境的差异,抵牾概念和定义带来的局限,以此延长每个意象能指的意义。
但是在《夜晚》中,毕赣有意地减弱了文本上的诗歌性表达,全片只有一句作为咒语的诗句———“你数过天上的星星吗?它们和小鸟一样,总在我胸口跳伞”;这句咒语贯穿了整部影片现实与梦境的交错过程,给予其唯一的合理性。由此,一句诗成为撑起电影整个虚幻梦境的悬置线。在《野餐》和《夜晚》中贯彻的诗性,可以用德勒兹的褶皱化空间理论进行解释。德勒兹认为世界是由越来越小的褶皱构成,褶皱的概念只存在于变化、变形和分叉之中,褶皱分离于世界原本的规则和界限,穿越至无穷的表现形象和无限自由的生存状态。这一理论打破了原始的理性结构与秩序,给予哲学家与艺术家意识结构的无序性以深切的合理性。
而毕赣的电影结构,也是在打破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理性秩序,他用非常规化的叙事结构分离思维中精确又紧密的逻辑性,留下足够的空间嵌入诗歌文本,填充每一处缝隙,并且将情感表征延伸向无穷无尽的感知层面,对观众产生移情作用。所有看似毫无秩序的符号、意象以及文字,都是失重的词语,等待着被嵌入诗歌的句式当中,它们被藏在每一个褶皱里,在梦境中接受精密的设计与编排后,构成一个完整的精神回溯过程。毕赣电影的这种诗性,一部分可以理解成“乡愁”,还有诸多其他的部分,如儿时记忆对他的潜在束缚、作为乡镇青年的空虚与无奈、自我建构过程中的不可调和、与世界产生的异化矛盾等等,这些情感共同促使着他在电影里试图去完成一种找寻与解答的过程,通过电影主人公的漫长追寻,来治愈他在现实世界中难以达成和解的“心病”,这是属于他的浪漫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而若是将这种诗意重新归位到乡镇情结中去,则是“小城镇不再是中国诸种社会问题的寄生土壤,电影对小城镇空间的表述也不再止于外部描绘,而是发展为植根于小城镇自身经验的话语呈现”
电影是“现实与想象的中转器”,兼具社会现象与美学现象。毕赣电影中的社会现象体现在故乡凯里的特殊地域环境和儿时父母感情不和的复杂生长环境中,美学现象则体现在他个人的哲学、文学与艺术素养,以及对情绪的敏锐感知力中。影片本身不仅仅是一场视听体验,更是抹去现实与虚幻边界的自我实践,化解真实世界的绝望感与无力感,让诗意呈现,一切各得其所。毕赣迄今为止现有的两部长片作品,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他特有的叙事风格与诗性表达,在中国乡镇电影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学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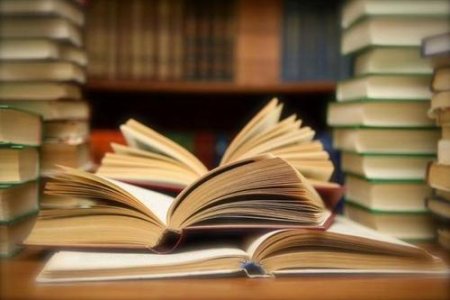
毕赣将这种族群地域特性作为构成其电影风格的重要元素,形成独特的电影话语。比如在视听话语层面上,镜面反射是毕赣电影中一个兼具技术性与文本性的表达手法。如在《夜晚》中,水面反射时针的拨动、湖面反射绿植的漂浮、后视镜反射人脸的悲怆,一切都敏感易碎,眼睛所见难辨真假,一切都只是宇宙的镜像。诸如此类的镜面反射也暗含了每个角色具有的双重意义:“万绮雯”和“凯珍”、罗纮武和“白猫”、白猫母亲和罗纮武母亲,他们之间都有着如同镜像一般真假难辨的共性与异性,一个角色承载着多重身份,暗含着多重时间线索,角色之间的身份关系就是影片文本的逻辑关系,这是毕赣电影中特殊的二重性乃至多重性的呈现。
另外,少数民族的地域性特色意象,如蜡染、芦笙、船只、苗乐等也多次出现在电影中,它们都将凯里营造出极致的孤独感和无法感同身受的忧思。而在诗性话语层面,诗意的表达是毕赣电影中最显著和独特的魅力。抛开导演和编剧身份的毕赣,也是一个年轻诗人,会将诗句适当地嵌入电影,使他的电影犹如诗集一般充满多样的解读,也平添了空灵气质。
电影《野餐》就是一部以诗歌连接场景的转换、用独白展现细微线索的作品。毕赣以贵州方言的诗歌旁白建立了电影话语表达的框架,用诗句为人物出场、时间线索、叙事细节一一定点。如“没有剃刀就封锁语言,没有心脏却活了九年”暗指陈升的九年牢狱生活,“手电的光透过掌背,仿佛看见跌进云端的海豚”解释前情中陈升对发廊老板娘的性暗示。毕赣还用陈升的第一视角来凝聚梦境,比如用手捂住手电筒的光,就是看到海豚的模样;陈升自述和妻子住在瀑布边,听不见彼此说话,只能跳舞;陈升坐在副驾驶与友人谈及曾经的牢狱经历。这些分解的叙事线索破除语言的逻辑性和排列秩序,模糊现实与梦境的差异,抵牾概念和定义带来的局限,以此延长每个意象能指的意义。
但是在《夜晚》中,毕赣有意地减弱了文本上的诗歌性表达,全片只有一句作为咒语的诗句———“你数过天上的星星吗?它们和小鸟一样,总在我胸口跳伞”;这句咒语贯穿了整部影片现实与梦境的交错过程,给予其唯一的合理性。由此,一句诗成为撑起电影整个虚幻梦境的悬置线。在《野餐》和《夜晚》中贯彻的诗性,可以用德勒兹的褶皱化空间理论进行解释。德勒兹认为世界是由越来越小的褶皱构成,褶皱的概念只存在于变化、变形和分叉之中,褶皱分离于世界原本的规则和界限,穿越至无穷的表现形象和无限自由的生存状态。这一理论打破了原始的理性结构与秩序,给予哲学家与艺术家意识结构的无序性以深切的合理性。
而毕赣的电影结构,也是在打破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理性秩序,他用非常规化的叙事结构分离思维中精确又紧密的逻辑性,留下足够的空间嵌入诗歌文本,填充每一处缝隙,并且将情感表征延伸向无穷无尽的感知层面,对观众产生移情作用。所有看似毫无秩序的符号、意象以及文字,都是失重的词语,等待着被嵌入诗歌的句式当中,它们被藏在每一个褶皱里,在梦境中接受精密的设计与编排后,构成一个完整的精神回溯过程。毕赣电影的这种诗性,一部分可以理解成“乡愁”,还有诸多其他的部分,如儿时记忆对他的潜在束缚、作为乡镇青年的空虚与无奈、自我建构过程中的不可调和、与世界产生的异化矛盾等等,这些情感共同促使着他在电影里试图去完成一种找寻与解答的过程,通过电影主人公的漫长追寻,来治愈他在现实世界中难以达成和解的“心病”,这是属于他的浪漫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而若是将这种诗意重新归位到乡镇情结中去,则是“小城镇不再是中国诸种社会问题的寄生土壤,电影对小城镇空间的表述也不再止于外部描绘,而是发展为植根于小城镇自身经验的话语呈现”
电影是“现实与想象的中转器”,兼具社会现象与美学现象。毕赣电影中的社会现象体现在故乡凯里的特殊地域环境和儿时父母感情不和的复杂生长环境中,美学现象则体现在他个人的哲学、文学与艺术素养,以及对情绪的敏锐感知力中。影片本身不仅仅是一场视听体验,更是抹去现实与虚幻边界的自我实践,化解真实世界的绝望感与无力感,让诗意呈现,一切各得其所。毕赣迄今为止现有的两部长片作品,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他特有的叙事风格与诗性表达,在中国乡镇电影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学突破。
妙高文案 专业化代写机构 一站式原创服务
为客户奋笔疾书 用文字创造价值
约稿电话/微信:18632160975
QQ:1392146
免责声明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网友上传(或整理自网络),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妙高文案网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